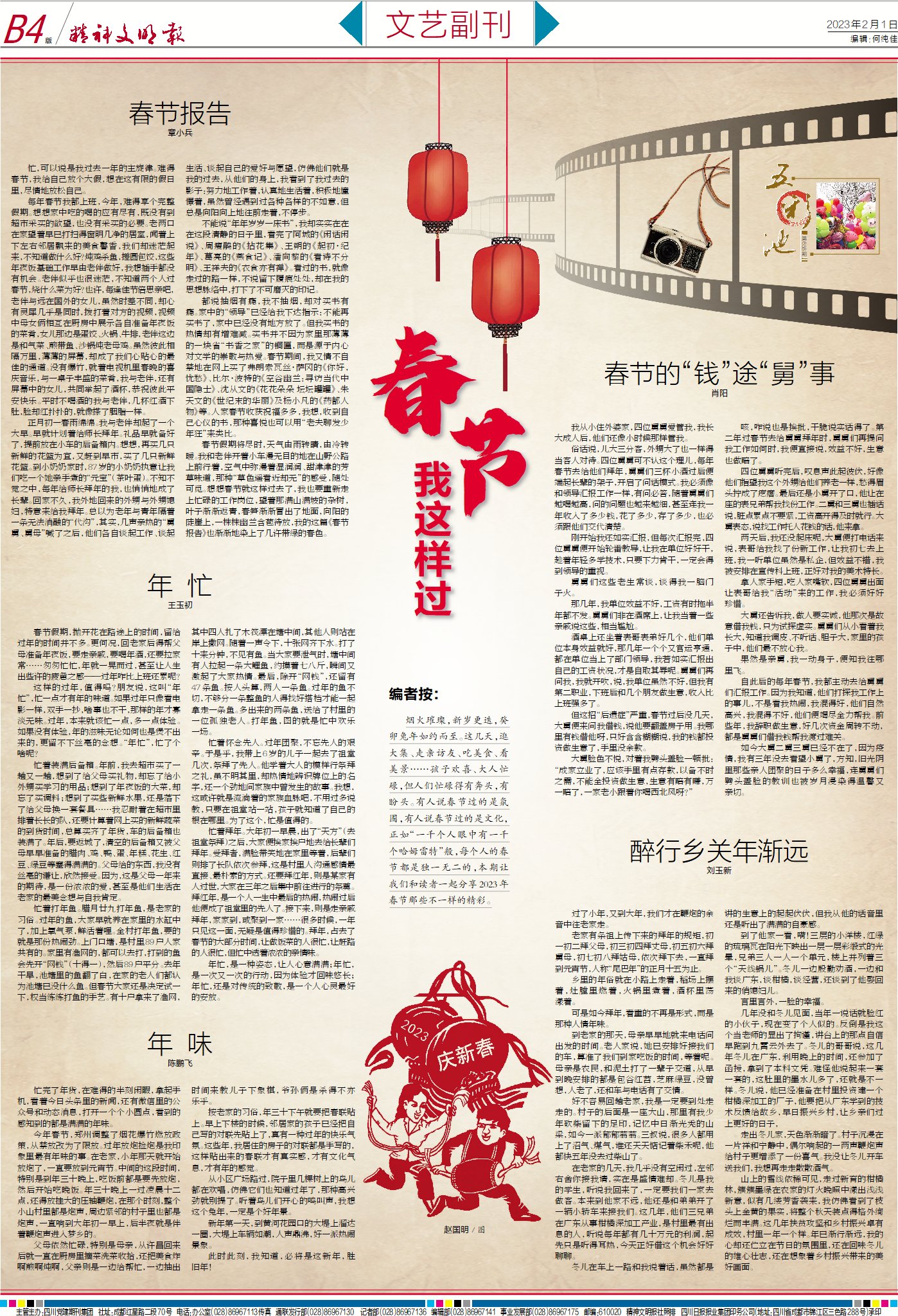|
||||||
春节报告
章小兵
忙,可以说是我过去一年的主旋律。难得春节,我给自己放个大假,想在这有限的假日里,尽情地放松自己。 每年春节我都上班,今年,难得享个完整假期。想想家中吃的喝的应有尽有,既没有到超市采买的欲望,也没有采买的必要。老两口在家望着早已打扫得窗明几净的居室,闻着上下左右邻居飘来的美食馨香,我们却迷茫起来,不知道做什么好?炖鸡杀鱼,搓圆包饺,这些年夜饭基础工作早由老伴做好,我想插手都没有机会。老伴似乎也很迷茫,不知道两个人过春节,烧什么菜为好?也许,每逢佳节倍思亲吧,老伴与远在国外的女儿,虽然时差不同,却心有灵犀几乎是同时,拨打着对方的视频,视频中母女俩相互在厨房中展示各自准备年夜饭的菜肴,女儿那边是蛋饺、火锅、牛排,老伴这边是和气菜、煎带鱼、沙锅炖老母鸡。虽然彼此相隔万里,薄薄的屏幕,却成了我们心贴心的最佳的通道。没有爆竹,就着电视机里春晚的喜庆音乐,与一桌子丰盛的菜肴,我与老伴,还有屏幕中的女儿,共同举起了酒杯,恭祝彼此平安快乐。平时不喝酒的我与老伴,几杯红酒下肚,脸却红扑扑的,就像搽了胭脂一样。 正月初一春雨绵绵。我与老伴却起了一个大早。早就计划着给师长拜年。礼品早就备好了,提前放在小车的后备箱内。想想,再买几只新鲜的花篮为宜,又赶到早市,买了几只新鲜花篮。到小奶奶家时,87岁的小奶奶执意让我们吃一个她亲手煮的“元宝”(茶叶蛋)。不知不觉之中,每年给师长拜年的我,也悄悄地成了长辈。回家不久,我外地回来的外甥与外甥媳妇,特意来给我拜年。总以为老年与青年隔着一条无法消融的“代沟”,其实,几声亲热的“舅舅、舅母”喊了之后,他们各自谈起工作、谈起生活、谈起自己的爱好与愿望,仿佛他们就是我的过去,从他们的身上,我看到了我过去的影子:努力地工作着,认真地生活着,积极地憧憬着,虽然曾经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不如意,但总是向阳向上地往前走着,不停步。 不能说“年年岁岁一床书”,我却实实在在在这段清静的日子里,看完了阿城的《闲话闲说》、周瘦鹃的《拈花集》、王朔的《起初·纪年》、葛亮的《燕食记》、潘向黎的《看诗不分明》、王祥夫的《衣食亦有禅》。看过的书,就像走过的路一样,不说留下履痕处处,却在我的思想脉络中,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 都说抽烟有瘾,我不抽烟,却对买书有瘾。家中的“领导”已经给我下达指示:不能再买书了,家中已经没有地方放了。但我买书的热情却有增难减。买书并不因为家里那薄薄的一块省“书香之家”的铜匾,而是源于内心对文学的崇敬与热爱。春节期间,我又情不自禁地在网上买了弗朗索瓦丝·萨冈的《你好,忧愁》、比尔·波特的《空谷幽兰:寻访当代中国隐士》、沈从文的《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》、朱天文的《世纪末的华丽》及杨小凡的《药都人物》等。人家春节收获祝福多多,我想,收到自己心仪的书,那种喜悦也可以用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来类比。 春节假期将尽时,天气由雨转晴,由冷转暖。我和老伴开着小车漫无目的地在山野公路上前行着,空气中弥漫着湿润润、甜津津的芳草味道,那种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感受,随处可觅。想想春节就这样过去了,我也要重新走上忙碌的工作岗位,望着那满山满坡的杂树,叶子渐渐返青,春笋渐渐冒出了地面,向阳的陡崖上,一株株幽兰含苞待放,我的这篇《春节报告》也渐渐地染上了几许带绿的春色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