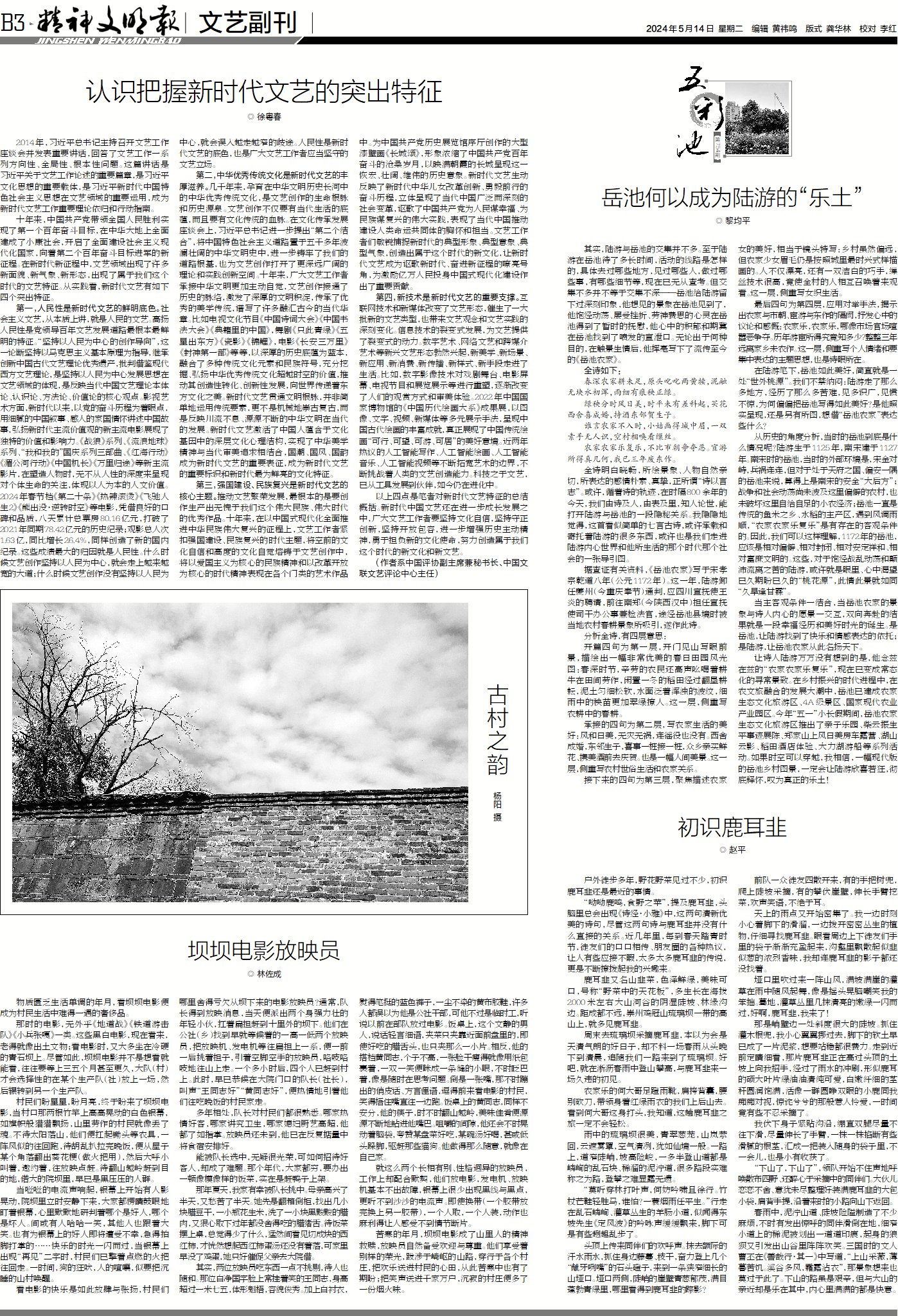|
||||||
初识鹿耳韭
◎ 赵平
户外徒步多年,野花野菜见过不少,初识鹿耳韭还是最近的事情。 “呦呦鹿鸣,食野之苹”,提及鹿耳韭,头脑里总会出现《诗经·小雅》中,这两句清新优美的诗句,尽管这两句诗与鹿耳韭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。近几年里,每到春天踏青时节,徒友们的口口相传、朋友圈的各种热议,让人有些应接不暇,太多太多鹿耳韭的传说,更是不断撩拨起我的兴趣来。 鹿耳韭又名山韭菜,色泽鲜绿,美味可口,号称“野菜中的天花板”,多生长在海拔2000米左右大山河谷的阴湿陡坡、林缘沟边。距成都不远,崇州鸡冠山琉璃坝一带的高山上,就多见鹿耳韭。 周末去琉璃坝采摘鹿耳韭,本以为会是天清气朗的好日子,却不料一场春雨从头晚下到清晨,追随我们一路来到了琉璃坝。好吧,就在淅沥春雨中登山攀高,与鹿耳韭来一场久违的初见。 农家乐的何大哥足蹬雨靴,肩挎背囊,腰别砍刀,带领身着红绿雨衣的我们上后山去。看到何大哥这身打头,我知道,这趟鹿耳韭之旅一定不会轻松。 雨中的琉璃坝很美,青翠葱茏,山岚萦回,云遮雾罩,空气清冽,犹如仙境一般。一路上,道窄陡峭,坡高险峻,一多半登山道都是嶙峋的乱石块、稀溜的泥泞道,很多路段实难称之为路,登攀之难显露无遗。 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行走在乱石嶙峋、灌草丛生的羊肠小道,似闻得东坡先生《定风波》的吟咏声缓缓飘来,脚下可是有些趔趄乱步了。 头顶上传来同伴们的欢呼声。抹去额际的汗水雨水,抓住身边藤蔓、枝干,奋力登上几个“龇牙咧嘴”的石头磴子,来到一条狭窄细长的山垭口。垭口两侧,陡峭的崖壁青葱郁茂,满目蓬勃青绿里,哪里看得到鹿耳韭的踪影? 前队一众徒友四散开来,有的手把树兜,爬上陡坡采摘,有的攀伏崖壁,伸长手臂挖菜,欢声笑语,不绝于耳。 天上的雨点又开始密集了。我一边时刻小心着脚下的滑溜,一边拨开密密丛生的植物,仔细寻找鹿耳韭。眼看周边上下徒友们手里的袋子渐渐充盈起来,沟壑里飘散起似韭似葱的浓烈香味,我却连鹿耳韭的影子都还没找着。 垭口里吹过来一阵山风,满坡满崖的灌草在雨中随风起舞,像是摇头晃脑嘲笑我的笨拙。蓦地,灌草丛里几抹清亮的嫩绿一闪而过,好啊,鹿耳韭,我来了! 那是峭壁边一处斜度很大的陡坡。抓住灌木根兜,我小心翼翼挪过去,脚下的软土早已成了一片泥浆,想要站稳都很费力。走到近前定睛细看,那片鹿耳韭正在高过头顶的土坡上向我招手,经过了雨水的冲刷,形似鹿耳的硕大叶片绿油油清纯可爱,白嫩纤细的茎秆圆润饱满,活像一群圆睁双眼的小鹿同我痴痴对视,惊诧兮兮的那般惹人怜爱,一时间竟有些不忍采摘了。 我伏下身子紧贴沟沿,绷直双腿尽量不往下滑,尽量伸长了手臂,一株一株掐断有些滑腻的根茎,汇成一把装入随身的袋子里,不一会儿,也是小有收获了。 “下山了,下山了”,领队开始不住声地呼唤散布四野、还醉心于采摘中的同伴们。大伙儿恋恋不舍、意犹未尽整理好装满鹿耳韭的大包小袋,肩背手提,沿着来时的小路向山下返回。 春雨中,泥泞山道、陡坡险隘制造了不少麻烦,不时有发出惊呼的同伴滑倒在地,细窄小道上的稀泥被划出一道道印痕,起身的狼狈又引发出山谷里阵阵欢笑。三国时的文人曹丕在《善哉行·其一》中写道,“上山采薇,薄暮苦饥。溪谷多风,霜露沾衣”,那景象想来也莫过于此了。下山的路虽是艰辛,但与大山的亲近却是乐在其中,内心里满满的都是快意。
|